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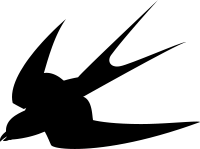


长崎
梅雨
眼睛一刹,已经到哉秋天了。但是我还没有写过长崎的梅雨天,实在是罪过。整个五六月份侪在忙考试啊学堂里的事体,到哉现在,几趟发表一过,又轧着期中正式生的发表会,我这杆「野路子」算是总算闲下来,没啥准备,黄梅天熟透的梅子也差不多盐成话梅了,帮诸君一人温二两黄酒,在冷秋吃了热洞洞,听我慢慢讲来。

梅·雨

讲到长崎的天气,伊跟江南比是实在正常不过了,但是放在中国大多数人的眼光下头,那是怪去怪来:啥个?一年里厢居然有得5只季节?岂不是倒反天罡?那不就是多雨的晚春嘛,有啥好讲的。恐怕大家侪会那么想。但是一翻开大作家余秋雨,朱自清的散文,在写这杏花冷雨的辰光,是拿伊归进春天的,突出一个「冷」字,上海人叫做「沁(读作饮)」,沁笃笃沁笃笃,沁到人的心肝里,沁不到人的骨头里。
而到了五六月份黄梅天的辰光,雨的性格变了,变得像是个跑了5公里的死胖子,你去鲜格格贴了伊身高头,又闷,又热,又一股肉夹气。此地讲究「春捂秋冻」,要是真到了黄梅天,啥人还管你捂不捂,恨不得统统剥光廿四个钟头孵进混堂去。所以,在上海人眼里,黄梅天是断称不上是春天的。
实际上,除掉地处温带的大陆之外,「一年四季」这个常识是不通用的,每个地方侪不尽相同,上海人头皮翘,硬劲是在春夏之间,插进去一个黄梅天出来。
不过,对于日本来讲,黄梅天的存在反而容易理解一点。不过,长崎的梅雨,帮上海比,也有伊自己的性格。总体来讲,长崎的雨更加煞劲一点,来哉排山,去哉倒海,一滴雨拍在脸上,眼睛一刹就浑身淌淌滴。肉眼可见的雨丝从天上连绵而下,落在家家户户棚顶上,滴滴答答,在落水处纺成棉纱线,织进浦上川。浦上川像是一只永不停歇的机杼,一路向天边交织着雪白的雨丝。等到纺成一匹成品,抬头一看:喔唷,居然是五颜六色的虹嘛。方才发觉,已经雨过天霁。到处侪清爽又漂亮,只有我头发塌光,胭脂糊光,裤子鞋子湿光,只好灰溜溜回转去调衣裳,调好又是一场新的雨等咾我,再浇我个托托湿。

梅·果

当时我齐巧在准备发表最忙的辰光,天天迎头一场雨迎头一场雨,居然一点没感冒,现在想想还是真的有点后怕。那么有人要讲了,这种天气你出去寻死啊?哎,诸君有所不知,讲到梅五月,必要吃一盘蓝白搪瓷盘里装的黄哈哈的枇杷,才算是过了黄梅天的瘾头。在上海,是必要吃洞庭山白沙枇杷,洞庭白沙分作东山西山两派,好送进上海的,基本是西山枇杷。季节一到,上海人就开始倾巢出动,开哉SUV咾面包车,有两只馋佬胚,一清老早跑去东方绿舟坐大巴士开到吴江再调车子,最后推兹个黄鱼车,也要去太湖拿两斤枇杷回来。长崎也是如此,只要是吃枇杷,非长崎县产的不吃,最最推板,也要吃大分产的广东枇杷。要是沾着一点茂木血统,那就是登堂入室,可以拿得出手送送人了,要是纯种茂木,也就是茂木町产的茂木品种枇杷,谁要是送你一箱,绝对是拿你当模子看了。
长崎茂木枇杷小悠悠一只,挑起来帮东山种的白沙有的一拼。白沙这只品种怪也是怪,别的枇杷,肉最好黄到发红,才算糖分浸出来了。白沙不一样,甜不甜不是靠看出来的,是靠捏出来的。最好的枇杷,捏上去正好可以帮大拇指同步:太硬,大拇指瘪进去,太软,枇杷瘪进去。这种捏的软硬劲,不分红肉白肉,是伲这种天吃星的拿手好戏。超市里进去一刻钟不到,就好拎兹一袋卖相挺刮的纯种茂木回转去了。从屁股头剥开,皮包,肉甜,核小,汁水滴滴答答,挂在胡子上,滴在瓷盘里,吃相难看的还有一滩在肚皮上。

梅·街

吃好枇杷,净了盘子,晶莹的水珠挂了盘子上,坐上吱吱呀呀的电车,晶莹的水珠挂了车子上。电车是两节生的,像是上个世纪上海的无轨电车,听大大讲老早去宝山上班,就是轧这种沙丁鱼罐头过去的,叮铃铃铃大转弯灯一响,总归有人皮鞋轧脱。后来上海有了地铁,就算又搞了71路,松江铛铛车,那种沙丁鱼罐头的感觉就已经是往事如风,散在城市的喧嚣中了。下了车,撑一把透明的洋伞,雨点毕剥毕剥打在伞面上,留下晶莹的水珠。
小学无数个期末考试的六月,我也这样看着雨点落在我的洋伞上,挂在548的窗上,挂在洗净的搪瓷盘子上,只不过这趟的终点,是新地中华街。
中华街上人山人海,开国语的,讲广东闲话的,讲日语的,讲英文的,样样式式的人撑了五颜六色的伞,开着国际玩笑从我四面八方穿过,我是啥人呢?我只是一个刚刚考试结束,心里七上八落去赴学期结束的饮酒会的「野路子」,我会在这里待多少辰光?天晓得。这趟面试和笔试写得怎么样?自己晓得。

梅·酒

去的人多,店又小,只好拆开台子坐。日本人客气,帮我留了靠里向的一桌,我到的最晚,也不是正式生,所以就坐了靠灶披间那头挨末席上。席间听老板娘叫人上菜,听到了长远没听到过的上海闲话。点饮料的辰光,考试过于紧张的挖塞帮不安,让我只想借酒浇愁。虽然大家侪晓得我出家门从来不碰老酒,但那一次,我破天荒地点了,温了二两黄酒。
黄酒漂洋过海,到了日本,自然也就变成洋酒了,一粒对半切开的青梅,浮在红亮的酒汤上。店里向是暖光的钨丝灯配着红木家生,借酒消愁变了太奢侈,只好慢下来慢慢咪。
老酒咪咪,山湖嘎嘎,期间老板娘也出来拿普通闲话跟我嘎了几句,讲她本来是市区里人,后来移民到长崎,年龄基本要翻我一个跟头了。同侪介绍,这就是中华街里叱仛风云,赫赫有名的春夏秋冬的老板娘。我问她,那么黄梅天呢?她笑了,指着我手里的杯子:喏,黄酒,梅子,天才。我讲,讲到中国酒,大家都只知道茅台知道白酒,托你的福,在长崎还好有得黄酒咪咪。端起杯子,我抿了一口。
平常甜蜜蜜的太雕,有了日本青梅的加入,变得来又酸又涩。我像是个熟透的红枇杷,被考试捏一下,被阵头雨捏一下,又被晚点的电车捏一下,捏得浑身都是乌青块。黄酒与梅子皆正宗,只有我这个天才是大兴货。五虚六肿的苦痛酸涩终于随着滴滴答答的雨声,沁进了骨头里,浮在面孔上。不和口味在日本是大事情,老板娘要帮我调一杯。我试探性讲了一句:不搭界的,就是在想心事。
「有啥心事啦,帮我讲讲呀,反正伊拉也听不懂的。」
我的面孔上落满了黄梅雨。
文字:淳于诺
排版:淳于诺
图片:淳于诺
